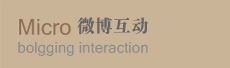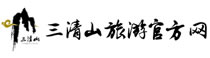在古窑与时光贴身而行
——摘自《瓷典》撰文/ 徐啸
景德镇是个不需要过多介绍的城市,城史千年,产好瓷。
每个家族里都有人从事与陶瓷相关的行业,在这里,陶瓷不是一门刻意需要攻克的学科,似乎与生俱来,像从母体中携带而来的DNA,每个人都可以对着你说出陶瓷的一二三四五。
如同弥漫在鼻息间的空气,目及之处也都有瓷器的身影。时光如水,在城市的肌理上默默流淌了千年,城市容颜已改,工匠与陶瓷之间的默契却还是最初的样子。
镌刻瓷史
清晨,枝叶上的晶莹露水抖落在一排木简上。晨练的人们也开始换上球鞋,钻进了树林浓郁的石砌小道,一边慢跑,一边端详木简上的刻字——“圆器青花:青花绘于圆器。一号动累百千,若非画款相同,必致参差互异……”
这些镌刻了制瓷流程的几十块木简林立在林子里和一条青石路旁,它们都是进入古窑的索引路线。
古窑艺术大门
我的古窑之行也是从这条古窑“柴”路开始,这个“柴”字有“柴火、人才、钱财”三层寓意。作为一个“签到式”景点,全国唯一一家以陶瓷文化为主题的国家AAAAA级旅游景区——景德镇古窑民俗博览区,环境和空间却足够让人放松身心,白云放浪漂浮,空气像一条清凉的丝带覆在鼻息,满眼绿植。
进入古窑景区,一条砌满了瓷片和瓷瓶的青砖路展现出来,砌在水泥里的瓷片还裹挟着从地底下挖出的泥土,瓷瓶的裂缝依旧还在,并没有进行人为的后期修饰。认识一位收藏家,每次他取出一样古物件时都十分虔诚,“有种跟一段历史对话的感觉”。陶瓷千年不变色的特质,让掌心贴近瓷面时,仍然感觉很温润。
瓷文化艺术休息景区
器物是记录历史演变的标本。所以,某种程度上而言,诚挚地面对一件古老器物,便是在与一段久远的时光对话。上面的尘土和破裂痕迹,更像是一种“保持原态”的诉说。当时的生产环境怎样?它从哪些人手中诞生?这些对历史追寻的问题,会自然地跃入脑中。
如果着迷于陶瓷历史,可以先从这些瓷片开始一段感性之旅。
行进大概10分钟,来到历代瓷窑展示区的第一个景“风火仙师庙”,其中供奉的是风火仙师童宾。明万历年间童宾舍生烧造龙缸的故事,如今在景德镇已是妇孺皆知。公元1599年,景德镇御器厂烧造大龙缸,龙缸又大又厚,烧造十分困难,一入窑经高温焙烧,不是变形就是坼裂。为了烧制成功,只有三十二岁的童宾跳进了窑火中,以身殉窑。也许是他的壮举感动了天地鬼神,第二天,当窑工打开窑门,一个晶亮璀璨的青龙白瓷缸惊现在大家面前,众窑工悲喜交加,一个个跪拜在窑前。
风火仙师庙
由于是御窑所在地的关系,景德镇的故事风起云涌。另一位与御窑有千丝万缕关系的便是唐英,唐英在景德镇督陶时间长近30年,是景德镇御窑厂督陶时间最长,成绩最显著的督陶官,使景德镇迎来了中国古代制瓷技术史的顶峰时期。为缅怀前贤,传承发展中华民族优秀文化,特建立了“唐英纪念馆”。
古窑景区内的“唐英纪念馆”
对于当时的御窑,民间有个说法“一窑百件瓷九成要砸掉”,从中就能想象到当时的挑选有多么严格。而景德镇如今尚存的“不计成本追求完美”的性格特质,或许与当时的经历也有着一衣带水的关联。
时光如水流过技艺却未渐行渐远
景德镇名声在外。所有人都听说过它,却不代表都了解它。比如“他们是怎样拉坯的?瓷器上的画面是如何画上去?窑长什么样子?”这些根植在当地人心中不以为然的东西,往往就是外来客心中挥之不去的好奇。
逛古窑的手工制瓷作坊,这些疑问都能得到完善解答。若有兴趣,还可以卷起衣袖,在旋转的轱辘车上,让瓷泥在手指间逐渐成形。至于是碗碟、茶杯还是瓶子,完全随你心意而定。
景德镇古窑传统手工制瓷作坊,由几栋穿逗式木构架建筑绕内院组成,踏进门,承袭了千年的制瓷工艺便全景展现在面前,踩泥、拉坯、印坯、利坯、挖足、施釉、画坯……各个步骤都在非常细致地展示,你可以凑到面前看,可以用相机记录下一块其貌不扬的瓷器逆袭成一件作品的全过程。
手工制瓷作坊
展示这些手工制瓷技艺的老艺人,都是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技艺精湛。
每一天,从拉坯的王炎生的手中,都会产出几十或上百个成型的瓷坯;每一天,在汪申芳画满青花釉料的笔端,也会有等量齐观的茶花碗诞生。有人描述景德镇“表面上看这仅仅是个非常普通的内陆城市,但只要在它的地面待够12个小时,你就能明白这座城市不凡的是它的市民,‘能在人间制造天堂的器物’。”当你目睹到他们与瓷土间的那份默契时,这句话就会变得很直观。瓷器画好后,便会运到一个庞然大物里。
非遗传承人——手工拉坯生产展示
非遗传承人——手工利坯生产展示
非遗传承人——手工施釉生产展示
非遗传承人——手工画坯生产展示
顺着手工制瓷的流程,我找到了几十米后的清代镇窑。那是座附着了很多柴火气息的建筑,灰色的砖墙,黑色的屋顶,沿着墙壁堆放的烧窑燃料——大量松木柴,流露出一种肃穆的感觉。
镇窑是迄今为止保存最完整,最具价值的古代瓷窑。它在1995年前一直维持正常烧炼生产。之后,由于各种原因,沉寂了10多年,由于没有正常的烧炼生产,窑体出现了自然裂缝坏损。几年前修复这座镇窑后,才恢复传统烧炼生产。
清代镇窑窑内
窑内分为两层结构,底层为装匣、开窑之用,二楼主要用来贮藏松柴。下雨天,一楼需要点灯,暖暖的灯光透过窗户和木头之间的缝隙向外传递光线,窑火香弥漫在一砖一瓦的每个角落,穿着布衣的窑工和他们的祖先一样在其中忙碌,安静地做着同样的工作。
清代镇窑复烧夜景
仿佛时光重叠了,镇窑仿佛已经不是座建筑,更是他们的时光旅行机器。
这座窑现在不常烧,一般一年烧制两次,但一窑可以烧制两万件瓷器。工作人员介绍,这一方面是为了延长它的寿命,一方面是因为燃料的可贵。虽然景德镇目前以气窑烧制为主,但柴窑烧造出来的才算精品中的精品。原因是松柴木中的油脂燃烧时会渗透到1300度的瓷器上,让瓷器的釉色散发出一种无法言表的美感。
复烧时,北京观复博物馆馆长、央视《百家讲坛》主讲人马未都亲抵现场,等待烧成好的瓷坯从匣子里取出,评定“完全和古代柴烧瓷窑烧出的瓷器一致,是不可多得的瓷器精品”。
马未都见证镇窑烧制出来的茶花碗
之后随清代镇窑一起被修复的还有明代葫芦窑、元代馒头窑、宋代龙窑、明清御窑等,它们就像是镇窑的兄弟,与它毗邻而居。
明代葫芦窑复烧夜景
元代馒头窑复烧夜景宋代龙窑复烧夜景
明清御窑复烧夜景
在水一方的繁华
像电视剧《青花》中表现的一样,过去,瓷器烧制好就会送去昌江码头。清园里一艘仿制的木船回溯了这段历史。
清园内的仿制木船
景德镇民间有句土话“船多不碍港”,形容当时码头的繁荣。“器行九域,施及外洋”。这是古人对景德镇瓷器遍于全国和世界这一情形的描述。明代科学家宋应星在著名的《天工开物》中说:“若夫中华四裔驰名,猎取者皆饶郡浮梁景德镇之产也。”
古时候,景德镇就是依靠水路进入了国际化轨道,那是在600多年前,由郑和协领下西洋。
还原水路运输之后,清园里再现了当时从采集原料、配釉的整个过程。比较于刻板的教科书,这里的展现方式要活络太多。
历史上,品质高端的瓷器一般外销。那么,制造精美器物的景德镇人用的是什么瓷器呢?
镇窑里,一位老艺人站在几排茶花碗前,旁边立着一块纸牌,上面写着“会唱歌的碗”,大概是接触了太多不可思议的目光,当我看着纸牌疑惑时,老艺人便将手指浸入一碗温水中,沿着碗沿摩擦,轻而易举的,一股清脆的音乐就尾随指腹的移动而不断变化,十分有趣。
外国游客体验会唱歌的老茶花碗
老艺人友好,邀我一起尝试。最初的几次都不得要领,之后竟也可以发出一些断断续续的脆响,再后也可以拉出一个长音。老艺人解释,这是柴窑烧制的手工瓷,所以能发出这种声响。
碗面的装饰是茶花,俗称“老茶花”,这是当年景德镇人家中的寻常之物,不过如今,价格已经翻了好多倍。
水上运输的历史留在了过去。但古窑在水边搭建了一个舞台名叫“瓷音水榭”,开阔了瓷器的另一种可能——瓷乐演奏。瓷鼓、瓷编钟、瓷磬、瓷笛、瓷管钟、瓷箫、瓷瓯——整套乐器完全以瓷器制造,由几人共同演奏。因为取材特别,现在这个乐团常常代表城市的名义外演。
瓷乐演奏
景德镇有首歌叫《我在景德镇等你》,其中有句歌词“古窑的神火通明千年仍不息,江南的烟雨隐约着飘逸,沉韵的伏笔染刻了传奇,前世心思化今生的胎记”,千年以来,这样的恋情还存在。一项手艺流传这么久时间,本来就算一段深刻的感情。
正所谓“岁月留痕”,对于任何人而言,“旧时光”是一种脑海里的影像,它晒在晾衣杆上,落在一砖一瓦的缝隙里,洒在一花一木间。能够成就一种熟悉感。对于当地人而言,制瓷影像天然形成于心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