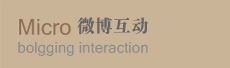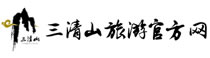坚守与传承,把桩师傅胡家旺之一

1300摄氏度的窑炉前,70岁的胡家旺躺在竹椅上,多数时候是在一口一口地喝茶。到了温度攀升的关键时刻,他一声令下,旁边的窑工便知道添柴加火。他坐的这把椅子,任何人不许碰,一碰就代表他可以“下课”了。他一个人在这把交椅上呆了20几年,他是一位了不起的把桩师傅。
体力劳动者里的将军
“十年可以培养一个博士,但培养不出一个把桩师傅。”胡家旺常念叨这句话。他如今天南地北地跑,靠的就是这项独门绝技。
在中国,从来没有一个城市能像景德镇一样,可以依靠一种产业维持生存一千年而没有中断。这里面,千年未断的窑火是重要因素。
景德镇传统制瓷包括柴窑烧成和手工成型两种技艺,即“烧”、“做”两大行。清代督陶官唐英说过一句话:“瓷器之成,窑火是赖”。没有窑炉,瓷器无从出生。窑炉就是瓷器的子宫。
瓷器好不好,往往就靠一把火,陶瓷因此被称为“火的艺术”。没有窑炉、没有燃料、没有技艺,也就出不来享誉世界的瓷器。所以说,景德镇窑炉发展的脉络,直接反映了景德镇陶瓷的发展史。
公元1712年,法国传教士昂特雷科莱在一封发往欧洲的信中表达了第一次踏上景德镇的土地时的惊诧,“白天从火焰和烟气的形状,就能看出它的轮廓;而夜晚,这里被火光包围,仿佛有许多烟囱的大火炉,神秘而美丽。”
恰恰也是这些传教士,将许多陶瓷制作的配方和技艺传到了欧洲。

“景德镇唯一没有流传到国外去的东西,就是这些窑炉。”胡家旺解释,古代只有来自都昌县和鄱阳县的人能烧窑,且要为冯、余、江、曹四大姓的人。否则,连窑厂都不能进。“柴窑跟景德镇发展息息相关,这里有世界上保存最完整、发展得最全的柴窑,也有最多的传统烧制技艺,但烧成技艺在景德镇一直是垄断的,外人见不了。”
而在欧洲传教士将景德镇的声誉扩大到世界几百年后,这里早已没有冲天的火光和烟雾,因为大多数的窑已经不再使用柴火,而是改为电烧或气烧。
“工匠八方来,器成天下走”一直是景德镇的立镇之本。不过,在现代陶瓷工业发达的今天,景德镇引以为豪的古老烧制技艺正在濒临消亡。并非四大家族的胡家旺,正是在这时成为了景德镇资历最老的把桩师傅,或者说,是最后一位。
“那些本该代代传承的人,多数中途放弃了,否则这事轮不到我去做。”胡家旺介绍,三四十年前,工匠便告诫子孙后代,“千万不要去烧窑。”
对于瓷器烧成,行业里有一句俗语:“一满二烧三歇火。”它概括了柴窑技艺的三个步骤,即码匣满窑、投柴烧炼和适时熄火。要掌握柴窑烧成的精深技艺,绝非一朝一夕可就,而是要一步一步学起。

胡家旺介绍窑工的等级时,翻开了自己一直珍藏的1963年景德镇烧瓷工艺流程表,上面写着柴窑工作有8个脚位,也就是8个等级,上三脚是把桩、驮坯和架表,下三脚是一伕半、二伕半、三伕半,中间有小伙手和收兜脚。其中,把桩师傅是柴窑烧成团队的技术核心,就像一只部队的元帅一样。1960年,把桩师傅一月拿93元工资,最低等级的一伕半只拿17元。
“‘把桩’是教不出来的,就像不可能教人当将军。可以说,100个烧窑的人,能出1个把桩就不错了。”胡家旺说。按照景德镇柴窑的规矩,厂子里的领导可以解雇把桩师傅,却不能单独辞掉里面的工人。把桩就像餐厅的大厨一样,上面的头不能单独把白案、红案给解雇了,有事都得找大厨。
历史上能干到“把桩”的人,都是从最低等级的一伕半干起的,一步步代替前面工位的人,才能最终登顶成为把桩师傅。“如果你哪样不会,就去指挥别人,人家会说,‘那你来干!’到时你能行吗?”胡家旺说,“就像军队里的士兵到将军一样,你得慢慢爬。”
如果窑烧得不好,烧塌半边匣钵是常有的事。“历史上整个报废的窑也有,前面温度高、后面温度不够,里面的瓷器都报废了。”胡家旺还记得景德镇一句民间俗语:“过的年好,不如建窑建得好,烧窑烧得好。”
作为烧窑总指挥,把桩师傅可以让老板发财,也能让窑厂倒闭。胡家旺每回干活前,小副手都先会把他的茶泡好、灯点好,再接他过来。开始工作前,他一定会沐浴更衣,这是老规矩。
柴窑的温度不平衡,温差大。前部的温度达到1000摄氏度时,后部才300摄氏度。这就要求窑工掌握好烧窑的快慢,把握好窑内的温度变化和气氛。颜色釉就是利用不同的窑位和不同的气氛烧制出来的。所以,烧柴窑全凭把桩师傅的经验。
“把桩就是要文武双全。”胡家旺说。首先,你得要有体力,能把几十斤的东西举起来,并把它们轻轻地码好,这就叫武功。其次,你得有眼力和判断力。“我能大概辨别温度,再来合理安排窑位。”凭借肉眼,胡家旺判断温度比景德镇陶瓷学院专家所设计的机械还准。

除了在观火口拿着草帽观火色外,把桩师傅还有“吐唾沫”的绝招。胡家旺介绍,一旦到了关键时刻,比如高温的时候,根据吐进去的唾沫燃烧程度,就可以辅助判断温度。“唾沫也是很讲究的。像我喝茶喝得多,唾沫中水分就比较多,因而对燃烧的状态自己有判断。”这种方式在胡家旺眼里,就跟中医闻大便、闻汗味一样。此外,在窑炉不同的部位,他还会放置一些试片,行话称“照子”,是用泥土做的,到时钩起来看看,对温度的判断误差就比较小。
正因烧窑时,胡家旺必须一直观察窑炉,控制投柴强度,所以他“每一刻脑子都在转,考虑着许多问题。”
胡家旺说,柴窑烧出来以后的陶瓷丰厚,釉质有玉质感,胎骨通透,“毕竟是慢慢‘煮’上去的,跟几下就好的烧窑方式不一样,就如大火和小火煮的东西不一样。”此外,因为柴窑内气温变化无常,柴窑烧出的东西气泡分布不均匀,跟“贼光”的气窑产品不太一样。
在建国瓷厂工作几十年,窑炉推倒重建了七八回,每次重建的资料胡家旺都好好保存了。他还记录了许多次烧窑的时间,以及窑位的放置。这些泛黄的资料,放置在胡家旺家里,记录了一个返不回的时代。